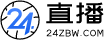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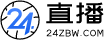

近日,效力于AC米兰前锋伊布接受了意大利《晚邮报》的专访。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球场内外的生活。采访部分内容如下:

伊布:这要看情况。不过最好不要在球场上说瑞典语,这种语言听起来太善良了,在球场上你需要更加邪恶一点。所以我认为斯拉夫语要更合适一些吧,有的时候也会说英语和意大利语。但我们在家都会说瑞典语、过着瑞典人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在进屋前要把鞋脱掉,只穿袜子。我们不会雇服务人员——只有一位清洁工,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自己来完成。
我确实是瑞典人,但我同样也是个混血儿。我的妈妈来自克罗地亚,她信奉天主教;我的爸爸是个穆斯林,他是波斯尼亚人;而我却在意大利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……
不,我只相信我自己。
不信。人总有一死,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希不希望他们给我办个葬礼,或者把我埋葬在坟墓里,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那些爱我的人感到痛苦。
完全没有。我甚至不喜欢听到别人跟我说“祝你好运”。我不需要好运,我自己才是那个决定事情将会如何发展的人。

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他们带着我在南斯拉夫坐过火车。现在想起来那似乎是另一个世界。
是个一直在受苦的孩子。我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被护士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。我一生都在受苦。在学生时代,我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长者金发碧眼,鼻子都很精致;而我的鼻子却很大,眼睛是棕色的,头发又是黑色的。我说话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,行为习惯也跟他们不一样,同学的家长曾申请把我赶出球队。总是会有人讨厌我,而且当时我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。我经常会被孤立。久而久之我学会了把痛苦和仇恨转化为动力。如果我心情很好,我的表现就会很出色;但如果我感到生气、受伤、痛苦,我就会用更好的表现来回应他们。球场里有很多喜欢我的球迷,我会从他们那里获得力量;但那些讨厌我的球迷会给予我更多的动力。
最近的一次发生在罗马。当我庆祝完进球之后,足足五万名球迷对着我喊“吉普赛人”。当时连裁判甚至都跑过来警告我。


种族主义无处不在,在我的家乡瑞典也会有这些。
非常羞涩。第一次跟人约会的时候,我甚至把我想对她说的话都写了下来。她说她想要聊点别的,但我还是在问她我刚刚写下的那些问题。那副画面简直惨不忍睹。我接触这些事都会比同龄人更晚一些。
是在我17岁的时候。因为直到我17岁那年,我才第一次走出了马尔默的贫民区,去了市中心。直到那时,我才认识到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瑞典姑娘都是什么样的——金发碧眼,观念自由。贫民区里的姑娘通常都留着短发、蒙着面纱。
她很珍重我,我又很有耐心。海伦娜比我大十岁,她当然会比我更加成熟。之后,我们又有了马克西米利安和文森特两个孩子。
可能是对阵英格兰队的那次距离球门30米的倒钩破门吧。当时英格兰人一直都瞧不起我,他们说我在对阵他们的球队时从来都没进过球……
当时玛丽娜-庞勒说要把我驱逐出境,我很害怕人们在大街上看到我会是什么反应。结果法国人跑过来跟我说:“伊布,你是对的,这里的确是一个很糟糕的国家。”
这没法比。孩子出生可能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,这是一个从你的生命中诞生的生命。我还记得当马克西米利安出生的时候,我把他抱了起来,紧贴我的胸口……我还记得当时文森特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过来跟我说:“爸爸,我想你了。”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。我恨不得立刻离开米兰、离开我所拥有的一切,然后回到他身边。
我之前尝试带他们去踢球的时候,其中一个小家伙哭了,另一个小家伙一直在观察天上飞的鸟。但他们现在都开始踢球了。他们在去试训的时候,原本想印上他们妈妈的姓氏——塞格,但这个名字似乎已经被占用了。现在马克西米利安决定要印上“伊布拉希莫维奇”了,文森特还没想好。
当时我爸爸过得非常痛苦,每天他都会听说有他认识的人去世了。他帮助了那些难民,他也想保证我的安全——他一直都想保护我。当他的姐姐在瑞典去世时,他不让我进太平间。但当我的哥哥萨普科死于白血病的时候,我就在他身边。哥哥一直在等着我,等我到了他面前之后,他才停止了呼吸。我们为他举办了穆斯林葬礼,爸爸当时并没有流泪,而是等到次日,他独自一人跑到墓地里去哭了一整天。
我当时没有找到对象,不仅仅是因为我很害羞,而是因为我爱上了我自己。我总是会在球场上尝试去表演一些杂耍般的动作,因为我比其他所有瑞典人加起来还要自恋。但我来到意大利之后,我改变了很多。我跟海伦娜说:“咱们总归要试一试。你跟我去都灵,看看咱们之间到底会不会有结果。”最终我们修成了正果。

是卡佩罗教会了我如何进球,他一直都在鞭策我。他是个强硬的家伙。在我来到他手底下踢球的第一天,在发布会和亮相仪式等等一些列工作结束后,我走进更衣室,看到他(卡佩罗)正在读一份《米兰体育报》。我很激动地跟他说:“早上好,先生!”然而他并没有放下报纸。我差不多在他旁边站了有一刻钟,紧张得脸都红了。然后卡佩罗站了起来,合上了报纸,径直走掉了。他当时一个字也没跟我说,就好像我压根不存在似的。